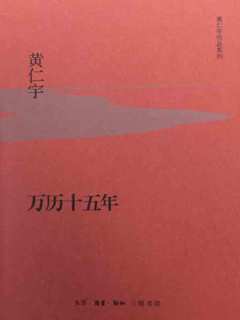历史
类型
9.0
豆瓣评分
可以朗读
语音朗读
204千字
字数
No.22
历史
2015-08-01
发行日期
展开全部
主编推荐语
黄仁宇明史研究专著,从万历十五年,俯瞰整个明朝的兴衰。
内容简介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作者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作者黄仁宇以其“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黄仁宇作品系列:万历十五年》中这一观念初露头角,“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黄仁宇作品系列:万历十五年》自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广泛的影响。
《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目录
-
版权信息
-
自序
-
第一章 万历皇帝
-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
第五章 海瑞 ——古怪的模范官僚
-
第六章 戚继光 ——孤独的将领
-
第七章 李贽 ——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
参考书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展开全部
跟不上时代步伐,结局可想而知
黄先生在文章结尾处的一段话,表明了作者对那个王朝那个制度的态度: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 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万历十五年》:在历史的齿轮间窥见文明的宿命
翻开《万历十五年》,我们触及的远非一段尘封的往事,而是黄仁宇先生以 “大历史观” 为手术刀,对大明帝国肌体进行的一次精妙解剖。这本书的魅力,不在于讲述六个历史人物的个人悲剧,而在于揭示了一种文明的结构性困境 —— 当一套高度道德化的治理体系,试图以其僵硬的教条框定复杂多变的人性与社会时,系统性的衰败便已成为命中注定的结局。一、 平庸年份的深意与 “大历史观” 的洞见 1587 年,表面 “四海升平”,实则暗流汹涌。黄仁宇选择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年份,正是要打破 “历史由英雄或重大事件创造” 的传统史观。他所倡导的 “大历史观”,要求我们将视线拉长放宽,从技术、经济、地理等长时段结构性因素中,探寻历史发展的深层逻辑。这并非否定个人的作用,而是将个人置于宏阔的时空坐标中,审视其与时代力量的复杂博弈。同年的西欧正经历大航海与宗教改革的狂飙,而大明帝国却在内部裂痕的悄然累积中滑向沉寂,这一对比更凸显了不同文明路径的必然分野。二、 困于系统的囚徒:个人努力的徒劳与必然书中的人物,无论地位尊卑,皆是被体制吞噬的悲剧角色。万历皇帝,作为 “活着的祖宗”,其悲剧在于他虽是帝国名义上的主宰,却不过是权力体系中最重要、也最被动的符号。他试图以 “消极怠工” 反抗文官集团用 “祖宗之法” 编织的囚笼,最终证明:在成熟的系统面前,即便是皇权,其力量也更多体现在 “否定” 而非 “建设” 上。他的困境揭示了最高权力的悖论 —— 权力的边界由其来源决定。首辅申时行的 “调和” 哲学,是在认清现实后的无奈选择。他深知在不触动系统根本的前提下,自己能做的只是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充当 “裱糊匠”,勉力维持帝国的表面平衡。他的智慧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其失败则印证了体制痼疾的深重。海瑞,这位极致的道德理想主义者,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整个官场的虚伪。他天真地将书本上的道德教条奉为圭臬并身体力行,结果却因过于认真而动摇了体制赖以运行的 “潜规则”,最终连 “为民请命” 的岗位都难以保全。他的故事警示我们,脱离现实感的理想主义,往往走向初衷的反面。戚继光的卓越,恰恰反衬了系统的失败。这位务实的行动大师,深谙在体制缝隙中寻找空间的艺术。他通过高超的人情练达与资源整合,在不改变现有资源的前提下,通过极致的组织化创造出强大的军事效能。然而,他的成功反而引发了系统的警惕与反弹,其悲剧结局表明,在一个为 “防止最坏” 而设计的系统中,“做得太好” 本身就是一种原罪。思想家李贽的激烈叛逆,试图打破儒家思想的僵化外壳,追求个性的解放与精神的自由。然而,他的批判武器仍来自传统,其思想无法被社会化与制度化,最终只能归于一种美学化的个人精神境界。他的痛苦在于,能敏锐地诊断出旧世界的疾病,却无力开出治愈的药方。三、 帝国的核心痼疾:道德理想与治理现实的断裂所有这些个人悲剧,都指向同一个根源:明朝的治理模式试图用一套单一的、定性的儒家道德标准来统摄一切社会问题。这导致了:1. 以道德代替法制:所有政治、经济、技术问题最终都被转化为道德争论,而道德争论无法量化,也无真正的胜负,只能依靠对礼仪细节的极端恪守来证明自身正确,从而阻碍了问题的客观分析与有效解决。2. 普遍虚伪的滋生:极高的道德标准与人性深处的私欲形成巨大落差,系统既不承认欲望的合理性,也未设立疏导规范之通道,导致 “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成为官场常态。3. “数目字管理” 的缺失:帝国缺乏精确的统计、会计与专业的司法体系,无法进行技术性的精细治理,只能依靠模糊的道德判断与宗法人情来维系,这使得国家治理始终停留在低水平循环。四、 历史的镜鉴:在复杂世界中寻求 “系统智慧”《万历十五年》留给我们的,远不止一段明史知识。它是一则关于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系统永恒张力的沉重寓言。它告诉我们,在强大的系统结构面前,个体的力量常常是渺小的。真正的智慧,并非手持道德洁癖去硬碰硬,而是深刻理解系统的底层逻辑后,在其中寻找行动的最大空间。这需要我们具备菲茨杰拉德所说的 “一流智力”—— 即在头脑中同时持有两种相反的观点,却仍能保持正常行事的能力。我们要学会在敬畏系统规则的前提下,追求现实的 “最大公约数”,以务实的态度、平衡的手腕,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推动善治的微光。最终,我们从万历的悲剧中领悟到,成熟的行事哲学,不是非黑即白的对抗,而是在深刻洞察人性弱点与系统规则之后,依然致力于在可能的范围内,有所作为,并保全那份最初的良知与理想。这,或许就是历史这面镜子,能照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光。
一本不可不读的历史书
这本书的出版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 石破天惊。这本书的价值体现在两个领域,首先在历史学的角度,黄仁宇在本书中提出大历史观,并指出中国之不能现代化,在于社会管理技术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
很多人以为,数目字管理就是数据化管理,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数目字管理指的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目的是让分散的社会资源产生聚集效应,比如银行就可以汇集社会资本并进行再利用。所以,黄仁宇在书中反复强调,中国以道德代法治的模式,在明朝到达巅峰。他并不是批判道德治理,而是指出道德治理的局限性。这个视角,是之前的历史书所没有的。
这本书的第二个价值在于写作模式和水平,用一句话来形容,这本书是非虚构写作的巅峰,至今也没有被超越。黄仁宇能把那无关紧要的一年写的引人入胜,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对我辈而言,是极佳的读物和写作范本。
因为以上两点,这本书在出版近 40 年之后,仍然是排名一二的畅销书,可谓经久不衰。
- 查看全部163条书评
出版方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简称三联书店) 是一家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出版社。 它的前身是邹韬奋、徐伯昕等三十年代在上海创立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