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这本书评了5.0
近代的职业劳动具有一种禁欲的性格,这想法本身并不是件新鲜事。断绝浮士德式的个人全方位完美发展的念头,而专心致力于一门工作,是现今世界里任何有价值的行动所必备的前提。对他(歌德)而言,这样的认知等于是向一个完美人性的时代断念诀别;这样的时代,在我们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已无法重流,犹如古雅典文化的全盛时期已一去不返。清教徒想要成为职业人(Berufsmensch)—— 而我们则必须成为职业人。如今,禁欲的精神已溜出了这牢笼 —— 是否永远,只有天晓得?总之,获胜的资本主义,既已盘根在机械文明的基础上,便也不再需要这样的支柱。其开朗的继承者(启蒙运动),似乎已永远地褪尽了她玫瑰般的红颜。“职业义务” 的思想,亦有如昔日宗教信仰的幽灵在我们的生活里徘徊。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赞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5.0修道院的生活样式不只丝毫不具蒙神称义的价值,而且更是逃离现世义务、自私自利、无情冷漠的产物。相反,世俗的职业劳动在他看来是邻人爱(Nächstenliebe)的外在表现,尽管此一见解的论据极为不切实际,并且与亚当・斯密的有名命题形成一种几乎是诡异的对比,因为他指出,分工迫使每个人为他人工作。这个本质上带有经院哲学风的见解,如我们所见,很快就再度消失了。后来的说法,并且愈来愈加以强调的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履行世俗内的义务是讨神欢喜的唯一之道,此一道路且唯独此道方为神之所愿,也因此,任何正当的职业在神之前绝对具有同等的价值。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赞分享「微信」扫码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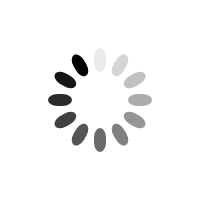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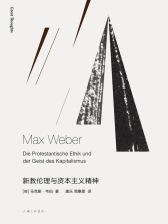 电子书
电子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版 理想国出品)
近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具有支配性力量的资本主义,何以独独从西方文明中孕生出来?韦伯从文化宗教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这一角度提出,近代资本主义以其理性化的持续经营和组织劳动为特征,而资本主义精神中的核心要素,即“天职”思想、为职业劳动献身的工作伦理,与基督新教的禁欲性格具有天然的内在亲和性。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派将工作奉为天职,有系统且理性地追求合法利得的人生观,正是资本主义发展最适合的精神动力。新教的人生观促进了基于职业理念上的理性化的生活倾向,如今,这已成为现代市民普遍的生活样式。虽然禁欲精神助长了近代经济秩序的诞生,但资本主义在建立起决定一切的秩序后,将自己的根基盘踞在机械文明之上,新教的入世禁欲精神,则解体为纯粹的功利主义。褪除了宗教伦理意涵的资本主义,最终走向“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的享乐人,这空无者竟自负已登上人类前所未达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