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这本书评了4.0对话,像温柔野兽。
先说为什么 4 星,因为期待太高了,也可能是这个时代我被视频打败啦。我对综艺有一种莫名的好感,奔赴远方,他们替你做到了。这本书相对应的综艺,和其他综艺不同,他们就是各个场景的对话。有时候看到,真是忍不住拍大腿,说得太好了。也就是那一句句太好了,看书的时候少了一点对方的惊奇的表情,所以略显不足,但内容完全没问题 (除了有几个错别字,都反馈了) 之前对许知远不是很了解,也没有什么好感,就知道他是懂文学的。后来被他那句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打动了。这也是接下来我想说的批评与赞美。对话中,好几次都感觉要 “聊崩” 了,许先生和嘉宾的对话,是那样的不搭,问的问题也很犀利。这里面的回答,是自己没想到的,蔡澜,罗振宇老师等等。许老师则是用一种近乎哲学的语言提问,对方的答案就构成了这本书的精华之处了。喜欢艺术的人大多会喜欢这本书,不装了,我就是艺术家的命,所以我也喜欢十三邀的对话,像温柔野兽一般。
1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15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4.0十三邀:我们时代的头脑与心灵人生轨迹中有无数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偶尔我们幸运的跟另一条轨迹志同道合一段,也许是半辈子,也许是半天,也许是半小时,都是礼物,值得珍惜。这本书主要是听完的,听书的效果没有自己读的好,印象深刻的人物很少。能记住的也就是:罗振宇老师、张艺谋导演、李安导演、罗大佑等这些相对熟悉的人。读这本是主要是为了了解人物事迹,看各个行业的人对知识的解读,对艺术的见解,对文化的看法,有不同的建议和解读才能引发讨论的热情,让思想文化更加璀璨。我在想等很久以后这些访谈作品会不会作为历史的一个小小的坐标,给在路上的人一些借鉴指导。目标不是一下就能达成的,是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学习修正的结果,所以我推荐翻翻看。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12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4.0单数十三邀。单读。单向历。单向空间。单数,带着一种义无反顾的孤独感十三邀的主持人许知远,是个留着长发习惯一脸严肃的作家,非典型知识分子,开着一家叫 "单向空间" 的书店。他极少访问当红明星,节目最常见的形式就是二人对坐,有时甚至还彼此沉默。画面没有任何特效,背景缺乏笑声。2005 年的年末,许知远和几个年轻媒体人在圆明园的一座院落里创办了 "單向街图书馆",名字取自德国思想家本雅明的同名著作《单向街》(One-Way Street)。许知远说:我想创造一种智识上的亲密感,一种 intellectual intimacy。所以也不见得说一定是实体的还是虚拟的,但它应该是某种空间,在其中发生一些智识上的交流,分享各种各样新的思想和书籍,这是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中断 也许意味着新的开端缓慢 未尝不是另一种速度最可怕的人生是丧失敏感性的人生而所有的穿梭陌生和失控都是对敏感性的重新唤起《十三邀》的片头文案第一季我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作家试图捕捉时代的精神却又常常厌恶时代的流行情绪我是个勉强的创业者努力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却又不完全相信商业的逻辑我还开一家书店书店里只卖我想看的书我对这个过分娱乐化浅薄的时代心怀不满希望打破大家思维中的惯性我也想了解这个迅速变迁的时代的新的动力新的情绪与人们内心的世界我会带着我的偏见出发等待这些偏见被打破或被再次印证。第二季我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作家着迷世界的复杂性与个体之间的力量我对技术、速度与娱乐驱动的时代持有怀疑我像个笨拙的发问者好奇他人的观念与经验我不喜欢模糊的立场却也怀疑过分确定的答案我期待自己是个游荡者不断拓展知识与情感的边界我也好奇在时代浪潮之中一些崭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正在被酝酿我会带着我的偏见与期待再次出发第三季每一次对话都是一次意外的相遇彼此的探测不可避免的不安以及自然到来的释然它令你重审自我一些时刻更为坚毅另一些时刻则充满怀疑它也催你质问生活之意义它也促你观察生活之矛盾高速变化的时代与个人意义危机的并存唯有更开放的对话更多元的思考才能追寻一种兼融之道在宽阔的世界中做一个不狭隘的人第四季看似静谧可能正澎湃表现的笃定其实充满不安理性才能拥抱危险历史与未来一样崭新而当下也许如过去一般古老以兼容之道编织意义之网老练亦可以很天真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10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5.0《敦刻尔克》很独特的一点是,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战争故事,它是一个有关撤退、逃跑和回家的故事。这群站在海滩上的人,他们直接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敌人的弹药,是战机轰炸和缺水问题,是对未知事物不断逼近的恐惧。我们试图制作出一部非常紧张的电影,把你真正带入海滩上的那群人之中,或者让你与火焰一起加入海滩上空的激战当中,这才是我们野心的真正所在。所以对我来说,这部电影对战争的态度是无意识的,我不希望它看起来是一部反对或者支持战争的片子,我希望它忠实于我对人类的求生、奋斗,以及人类如何应对巨大压力的感受。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10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4.0每日一书:《十三邀》。人生轨迹中有无数擦肩而过的陌路人,偶尔我们幸运地跟另一条轨迹志同道合一段,也许是半辈子,也许是半天,也许是半小时,都是礼物,值得珍惜。我总渴望另一种人生,水手、银行家或是一个摇滚乐手,总之不是此刻的自己。采访是满足这种渴望的便捷方式,在他人的故事中,我体会另一种生活,享受暂时遗忘自我之乐。尊重历史不是说一切都绕不开过去 —— 你要尊重它,因为它是来源,你今天的问题就出在过去。但是检讨历史,也要记得我今天的所作所为是要负责任的,不是我两手一伸就没事了,下面听我话的人监督我,我也要对他负责任,不能乱说。我最信任中国人自尊自重。中国人注重的是 “气”,天地间的正气,每个人身上都可以禀赋到一点,这个正气就是 “神”。不是具象的神,不用祂来吩咐你,你不做事我赶你出伊甸园,而是你自己培养自己。我是宇宙之间的人,每个人心里存在着这个,人为大,我不自尊,人家谁会尊敬我。所以人接受教育,不是说你受的教育换得吃饭的工具,也不是说受了教育知道人跟人怎么相处,而是要有一种教育,使人养成一个远见,能超越你未见。我们要想办法设想我没见到的世界还有可能是什么样,去扩展可能性,可能性是无穷的。乾隆盛世是中华文明衰落的起点。我觉得曹雪芹不是凡人,不是我们人间的人。他有直觉的敏感,写的不仅是贾府的兴衰,更是他对整个文化、历史、传统的第六感。我想曹雪芹已经感受到我们那个大传统的衰落。《红楼梦》不是讲了,贾家兴盛了百年,有一天要树倒猢狲散。我想他看到乾隆朝表面的繁荣,心里已经意识到,这个荣景真的有一天会往下降。他受佛家的影响很深,对人世间的苦乐无常,感受一定深得不得了。所以我觉得《红楼梦》是一首史诗式的挽歌,哀叹的不仅是十二钗。《红楼梦》以后,没有一本书达到它一半的高度。整个民族的创造性突然衰竭了,不光是文学,各种领域,我们的绘画,我们的陶瓷,从乾隆以后通通往下走。王小波说他把人分成我们的人和他们的人,《我的阴阳两界》其实就是说有些人一看就是我们的人,有些人一看就是他们的人。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世界上,粗浅地分,有一部分人追求功名利禄,物质或者权力;有一些人追求精神层面,知识、智慧、艺术。那么我顺着我的喜好活下去,其实也是很有意义。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能力和爱好,是相当强的。但是科学思想上的改变,基本没中国人什么事。哪怕到了二十世纪,中国人已经开始介入科学研究,这种基本科学思想基本全是西方人在做,日本人在做,没有中国人什么事。城市就是这样,就像一个森林,破坏了以后,过几年,它又长满了各种植物,又包裹起来了。城市的魅力就在这种地方,不是一目了然的,那才带劲,对吧?到处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要保持这个生态,不能够把它搞得像一个军事化的生活方式。也是博尔赫斯讲的,有时你会模仿一个人讲话的语调、姿势,甚至扩展到文学书写,是因为你想像他那样想事情,想站到他那里去看他看到的东西,这才能让你突破有限的、在此处就不能在彼处的、成为这一时限就不能够成为另外时限的那种生命的局限与单调。其实主要还是从这些富有的社会、发达的国家,包括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言外之意,那些穷的、买不起东西的贫困社会的人,对他们的影响怎么样,跟世界经济是没关系的;他们遭遇再怎么惨,对世界的影响不会那么大,所以没有几个人花心思、花时间去过问、了解。我在《唐诗的读法》里写到,庞德和李白在他们的时代,一定是不讨人喜欢的,就那么几个人喜欢。莎士比亚很伟大,但莎士比亚当时就是一个向上爬的人,一个商业作家。莎士比亚的写作里为什么有那么多噱头?就是因为他要把人吸引到舞台边上来。所以宫廷趣味是拒绝莎士比亚的,他们认为莎士比亚是野蛮人。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中华民族的探文明工程,包括我个人做的这种早期中国研究,是一种学术上的寻根问祖,是带着情感来做的。有利的一面是,一旦进入民国大家的法眼,才能从此结束甲骨文在中药铺里被碾成中药那样一种命运。不利的一面是,我们可能融进了过多的情感,在我们百年以来的探索过程中,救亡图存、民族主义这样的一种情怀和科学理性之间能不能和谐地契合起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民粹主义一定是与精英主义结合的,民粹主义的背后都是精英主义。民粹主义就是精英分子直接代表民众,否则是没有纯粹的民粹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对立面是什么?是中间。民粹主义,就是因为中间消失之后,这两极直接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与学生进行互动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在聪明的年轻人群体里尝试一些新想法,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索不同的东西,这与参加电视访谈或者会议有很大的不同,在那些场合中你不能做尝试,你必须确切地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且,我发现教别人能够真正证明你是否理解了这些东西。当你尝试向别人解释一件事而别人不能理解时,这通常意味着其实你也不理解。我们花了一百年的时间认识到,那个中央集权制度是需要改革的,然而 1927 年以后,我们又重建了这样一套集权制度。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梁启超说谭嗣同是清末的一颗彗星,很亮,很耀眼,一下子就划过去了。其实我们不希望有这样一个人物,对个人是一个悲剧,对时代是一种浪费。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9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5.0打开格局,拥有更多看世界的视角我以前对于访谈有偏见,我觉得访谈过于肤浅。现在看来是我太肤浅了,访谈的深度与访谈者和被访谈者有关,也与他们的思想碰撞有关。许知远的水平不错,他选的访谈对象的水平更不错,我不得不承认是我的格局太小了。一、访谈让我看到了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标签。王石: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头一贯看不起商人,这个让我焦虑了很久,而且我能感觉到文化人骨子里对商人是有一种鄙视的,更不要说平常得去打交道的官僚系统,他们也有,我对这个非常敏感。当然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并不是说因为他们看不起我,所以我也看不起我自己。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格局,原来世人眼中的成功商人,竟然会有这种感受,我突然之间觉得格局打开了。王石竟然觉得在哈佛完成学业比攀登峰更难,他把完成学业称为登无形的珠峰,他觉得他是在哈佛重生的。他说:“你登珠峰也就熬两个月,而在学校这儿熬着,第一,没头儿,第二,能不能完成,能不能真的顺利度过去,你不知道,甚至做作业要做到凌晨两三点钟,早晨七点半就起来,因为早课是八点。那时候人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状态,你就会思考你再这么熬到底值不值得,你只是访问学者,又不是要拿个硕士或者拿个博士,你晃晃就回去了,要蒙混过关其实很容易的。但我的问题是,放弃了会不会后悔。我六十岁才到的哈佛,如果放弃了,我不可能等六十五了再重来一次,我担心我到那个时候会后悔,后悔当时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下。” 看了这段话以后,我突然意识到我不应该用一个个标签是定义名人,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人会有挣扎,人会有欲望,人会想放弃,而贴标签会让我产生偏见。王石谈到的个人英雄主义也挺让我感慨的。说句真话,我根本就不想点开王石的采访录,我无意中点开了,竟然对他的采访很有共鸣。我们或多或少都是有点个人英雄主义的情绪的,如果才能放低自己的位置呢?王石的经历让我陷入了思考,虽然他并没有给我提供一个答案。那到底什么时候需要个人英雄主义?什么时候个人英雄主义是一个混蛋呢?“我 2001 年就开始划赛艇,划赛艇的时候也是个人英雄主义。本来是八人艇,我却不和队员们合练,从本质上来讲,这根本不符合划赛艇的精神,划赛艇就是要一块儿练,需要互相配合。真正到剑桥之后,这就是人家剑桥体育的一个招牌,我自然而然地就被纳入这个系统了,才发现我和人家比,年龄、经验,各方面都不如。在中国文化里,你是老板,你来了,第一是欢迎你,第二是迁就你。到了剑桥谁迁就你?人家即使迁就你也不是因为你是老板,而是因为你的状态。但我发现进入这个团队之后,人家却能让你很舒服,而不是说要让你难看,显得你不如别人。人家就是照顾你,因为你加入了就是属于这个团队的,队员们更多是在你最好的状态下慢慢跟你配合。人家不把你当成弱者,划赛艇的精神本身就是要齐心协力,在齐心协力的情况下,每个人的状态都很好。于是你突然发现,现代工业文明中最为典型的协作,强调的更多是整体,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慢慢融入这里之后,我才体会到,划了十二年赛艇,我整个是个混蛋。” 二、访谈让我看到了各行各业的不容易。《十三邀》中有很多人我并不熟悉,我首先点开的是罗振宇的采访录,毕竟这个胖子曾经是我的偶像。我现在有一个执念或者说一个原则,点开一本书,无论这本书我多不喜欢,我都要强行看完,我想让我的大脑具有更高的开放性。但这并不代表我要全盘接受这本书的所有观点,只是我害怕我自己只看自己喜欢的内容,永远待在自己的舒适区。有了这个开放性以后,我反而有了意外的收获。我看了许知远采访著名的考古学家许宏,在此之前我并没有听说过这个人。许宏曾经在一个基地培训过。那个基地晚上门一关,整个就像牢房一样。晚上上课,半天一个人,两个探方,教官非常严厉,你错了什么东西都及时指出,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二十多个人,每届一定要有三个不及格的。山沟里到汽车站很远,中间不准回去。这种班肯定不会给你找好挖的地方挖,四米乘四米的一个探方,两米多深,到最后三十三个灰坑、烂泥坑相互叠压。铁杆考古人必须经历过这个。我以前还是脸谱化个人了,现在能够通过采访看到更多的细节,薇娅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有血有肉,她更像一个亲切的邻居,而不是一个网红。我能够理解她,她想成为广大网友的陪伴。她也想在直播间开开玩笑,放慢节奏,但是网友不买账,网友催她赶紧上链接,迫不及待想买东西,她应该也有失落吧。当北大荒集团建议她尝试卖一下大米的时候,她只是想尝试一下,没有想到被网友骂得很惨,骂的内容是 “卖衣服就好了,卖零食就好了,现在还要卖大米,是不是想赚钱想疯了”。实际上那一场直播她一分也没有赚,只是当成一个业务拓展而已。网友躲上电脑后面,道德感薄弱,畅所欲言地说出自己的感受,相信对于薇娅而言众口铄金的感觉并不是很好。她原本出于好意想做一下公益,她的直播间突然多出了很多负能量的东西,骂她作秀,说 “这个地方真的穷吗,还没有我们老家那儿穷”。还有人说 “你做公益,你自己捐钱,干吗要让我们去买,你道德绑架”…… 那次直播,她当时差点没绷住。因为整场直播,大家都在怀疑她的人品,就这点她接受不了。这些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让我很敬佩她,这姑娘心态真不错,她得有多强的情绪净化能力。公益事件之后,她还进行了复盘,分析了自己招骂的原因,直播还是必须以产品的质量为主,以产品为主,不用管是扶贫还是不扶贫,不能道德绑架网友。三、访谈让我拥有了更多看世界的视角我个人非学肤浅的,我是被娱乐圈的人吸引进来的,第三本书里面的人物我完全没有听说过,但是我发现第三本对我的收获却最大,第三本书仿佛给我找开了新天地。这本书中采访的对象有哲学字、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诗人、人类学家等等。这些领域的翘楚我了解得非常少,虽然这些人的访问领悟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还是很开心就站在门口往里面瞧一瞧。关于陈嘉映我印象深度的观点有 “科技改变写作习惯”:电脑写作就改变了我写作的方式。你看古代人写的信,像范文似的。他的思想习惯,就像我们年轻时候的思想习惯一样,是把句子都组织好了,甚至把文章都组织得差不多了,然后落笔。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因为修改起来太容易了。这肯定会影响你想问题的方式。关于考古学家许宏我印象最深刻的观点是 —— 学界应该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我深切地意识到我们六零后就是给年轻人搭桥铺路,只能是过渡的一代。现在年轻的学者有许多自己的独立思考,但是他们没有话语权,我们应该给他们开路,而不是有意无意地限制束缚他们。按我的归纳总结就是迎接学科断奶期。以前是不用年轻人自己想的,有一个领袖式的人物,是你尊敬的师长在引导你。现在我管它叫后大家时代,进入社会考古组建的阶段,相当于西周一统王朝变到春秋战国的分裂状态,领头羊没有了,但是这种学科发展方向的多元化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吗?不光是考古学科,整个学术界的学术权威都在丧失。许宏老师的思考和坦诚让我很敬佩,可能人到了一定的年纪都会明白,自己只不过是给年轻人搭桥铺路的,自己只不过是过渡的一代。发展心理学也说这段人生旅程的主要任务是繁殖,这里的繁殖不仅仅是生儿育女,还包括培养和帮助下一代。但是很遗憾的是很多人并不服老,也不想完成自己人生的使命。关于人类学家项飙给我的最深感受是,原来人类学是如此的贴近生活,原来人类学在生活中竟然如此有用。对于项飙的采访讨论了很多现代生活话题,我才明白了人类学研究的内容如此接地气,人类学竟然是一门如此实用的科学。项飙有个观战让我觉得挺有启发,他说人们渐渐忽略了 “附近” 这个概念。许知远说:“有次我去苏格兰玩,要找一个公园,就找到一个当地人问路,他特别有趣,对自己周围的环境有清晰的认识,会告诉我周围那些地方的历史,好像很有意愿启蒙你。但我们在这方面普遍挺弱的,你去问路的话,会发现他对周围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尽管他在那儿可能待了很久了。” 项飙认为中国人对自己周边世界没有形成一个叙述的愿望和能力,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人有一种超越生活的愿望。年轻人对自己所在的小区不敢兴趣,因为他觉得这不重要,但他却对世界大学的排名感兴趣,因为他只想超越。有时候不仅要逃离自己的生活环境,自己的小区,还要完全逃离自我,而且喜欢对大的事情发言。这让我突然想到了 “诗和远方”,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经常把 “诗和远方” 挂在嘴边,因为我们对现在不感兴趣,我们只想超越现在。我们喜欢对大的事情指指点点,唯独对现在不感兴趣,这真是一个挺有趣的现象。就像项飙说的一样:“有的时候他一下子跳出来,对一个宏大的事件做很宏大的评论,但对附近没有兴趣。他只对家里头感兴趣,要不就是全世界。” 我们这一代人只对家感兴趣,要不就是全世界感兴趣,反正我们不对附近产生兴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最后我想谈一下我通过《十三邀》发现的宝藏人物 —— 赫拉利。他是《人类简史》的作者,但是我地他提起兴趣的却是我在采访中发现了他是一个同性恋。而且他还对此振振有词:“对于同性恋身份的自我认识从小就让我明白,不能完全相信大众或社会的认知。我还很小的时候,每个人都说男孩应该喜欢女孩,女孩应该喜欢男孩,这就是规律,这就是世界。你可能会认为他们一定对此十分了解,因为他们又年长又充满智慧。但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不,情况并非如此,我虽是一个男孩,但我被其他男孩吸引,而不是女孩,这就是现实。最终我得出结论,人们必须切合现实,而不是做社会告诉你应做的事,社会往往非常具有误导性。” 他的这翻言论让我拥有了一个新的视角,他的同性恋身份竟然能够让他知道不能完全相信大众或者社会的认知。他对于乔治・奥威尔的不屑一顾让我大吃一惊,乔治・奥威尔可是写出著名的《1984》的作者啊。他是这么说的:“乔治・奥威尔就属于无趣的科幻历史作家,他的《1984》是无趣的,因为你能很明显地看出来它刻画的是一个很糟的地方,是我们不想变成的情况。这种作品能引发人们思考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阻止坏事发生,所以从脑力上讲不是很有趣。” 他这段话让我特别不服气,我去看了他写的《人类简史》,我竟然被深深迷住了,他说得真对,我真香了,他写的书确实很幽默,而且他热衷于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人类学、生态学、政治学、文化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角度,对作为一个物种的智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来龙去脉,做出全方位的考察和预测。老实说,如此大规模跨学科的史学研究计划是令人瞠目的。能够像他这样从容游走于这么多学科之间的历史学家,是旷世罕见的。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18分享「微信」扫码分享 - 加载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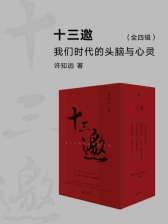 电子书
电子书十三邀:我们时代的头脑与心灵 (全四辑)
关于成功,也关于失败的艺术,关于符号与表达,也关于偶像与浪潮,关于时代大问题,也关于另辟蹊径的小注脚,关于知识和审美,也关于个体的多种可能性。关于与过去的人和解,也关于什么样的生活值得过。 关于史学大家许倬云谈论年轻人应该如何安顿身心、安顿自我,也关于人类学家项飚对我们生活中“附近”消失之后的理解与新的建议;关于功成名就后的艺术家,如何看待创造与失败、艺术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关于我们时代最知名的知识者如何谈论价值,寻求理解,提出问题…… 《十三邀》,是著名知识分子许知远与我们时代中各行业、各领域内最具典型性的样本人物所展开的一场盛大对话。他们各自以独有的视角,在个体与时代、智性与审美、自我与世界、见识与创造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对话与交流,共同对个体与时代做出的观察与思考,全面展示出我们时代最优秀的头脑与心灵对历史、当下和未来做出的追问和探索。 通过《十三邀》,我们阅读到52段故事,体会52种人生,游历52种交错的时间与空间,遇见52种立场和价值,它不仅是一个访谈,更像是一种旅行。 与视频节目不同,图书版《十三邀》打破了1至4季的区隔,重新划分为艺术界、演艺界、人文知识分子、时代浪潮人物等四大领域,使得每个领域的意见、经验与心得更加具有模板作用,以不同领域中正在发生的样本,探求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切片,进而带领读者在这些对话的碰撞中重新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也正因这样精彩的对话而变得魅力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