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这本书评了4.05-2-14 奇葩说后的擎师
这期的《第一财经》和得到的相关度比较高。有谈到豆瓣,B 站,奇葩说等平台和节目对文化领域的影响。主要聚焦的人物还是最近突然 “爆红” 的擎师,记得在#西方现代思想#课程刚上线的时候,寂寂无闻,顾衡还在城邦惋惜 —— 好内容没有人重视。恐怕连擎师自己也没有想到,半年后能如此受年轻人的欢迎。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如此优秀的学者能够在年轻人中间产生巨大影响力和积极的作用,比深陷在微博 “战场” 中要好的多。但学者 “商业化” 的确也存在很多负面影响。我也非常喜欢刘擎老师,希望他能够适应新的生活,持续带给我们深入的思考和新的启迪。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21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4.0这代新青年,也出现了 “知识饥渴” 这两年,年轻人非常喜欢学者,我想讨论下这个话题。这两年,像刘擎这样忙起来的 “网红” 教授不在少数,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罗翔,从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离职的薛兆丰,远在欧洲钻研人类学的项飙,加上之前已走进公众视野的陈嘉映、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清华政治系副教授刘瑜等等,不一而足。视频网站的流行,在经过大量无脑视频的轰炸以后,现在的年轻人开始转折吸收一些有营养有知识含量的视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让一部分学者先红起来,有何不好😎,我也是看了奇葩说之后,才喜欢上了罗振宇老师,才进入了得到这个大家庭,谁说学者一定要锁在象牙塔里?😤
1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116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4.0知识偶像觉醒的反思看最新的一期《第一财经 (月刊 2021 年 05 月)》,发现主要内容就是探讨在新时期随着互联网走进新青年视野里而爆火的学者们以及背后反映的社会现象。像 “法外狂徒张三” B 站知名 UP 主罗翔、“把自己作为方法” 人类学家项飚、在《奇葩说》走红的经济学教授薛兆丰和政治学教授刘擎、还有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清华政治系副教授刘瑜等等。这些都是这几年新起的知识偶像,细数下来几乎每一个我都有关注。像世界读书日的时候我会在 B 站等罗翔老师的分享、会看他在吐槽大会里大杀四方、会读他推荐过的书。时常回想起罗翔老师在十三邀里说的话:“人要接受自己的有限性,承认自己的逻辑是有限的,承认自己的理解是有限的,承认自己的阅读是有限的,我整个人就是在偏见之中,我的一生就是在走出偏见。” 这种自觉和理性,真的非常让人钦佩。还有项飚老师,我花时间完整的录读过他的《把自己作为方法》,就还挺耗时间和精力的,虽然忘掉了七七八八,但是这本书是我 2020 年觉得最精彩的书。还为他看过《十三邀》里面的内容,关于 “附近” 的概念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人们对于附近发生的事情无知无觉、毫无了解的兴趣,却对很大的、很远之外的世界充满热情,中间层就像隔空消失了。就像我对于隔壁邻居、所在社区漠不关心,却对发生在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异常关心。总觉得自己能够改变一些事情,只要努力的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其实这是个幻觉。我们每个人都只能感染或者影响到那些朝夕相处的人,隔着遥远的互联网,我们只能在原地成为某种事件里的流量,贡献着没有多大意义的呼喊。—————————————————— 其他学者或多或少的都听过他们在网上流传的各种讲座和开设的栏目。细细回想过来,我也是这个现象的参与者和受众,真实的体验过这一文化繁荣。知识偶像受到追捧加上又是 5 月份,外加我刚看完《觉醒年代》,不由得让人想起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那年的学者们作为青年人的引路人,推动着青年人对于中国与世界、社会与革命的思考。以亲身经历来寻找救国方法、探讨新旧文化和组织社会实践。寻找一种新的理论来指导实践,这就是《觉醒年代》里始终围绕的主线。而如今,百年已过,大家为什么又重新需要这种知识偶像呢?我自己想应该有两点。首先就是 “附近” 的缺失。互联网取代了很大部分本该有社区提供的一些服务,让更多的人成为互联网的触角的末端,减少了和不同阶层互动沟通的渠道,让社会养育很大程度转变为互联网、电商养育。就像我现在都很少去实体店买东西了,除非是和朋友约好了一起出去逛街。如非必要,基本上都是通过网购解决。附近应该如何运作、社区有哪些变化、周围有哪些菜市场、哪里的人最友善,这些无人关注的问题慢慢的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整一个周边的环境正在消失于我们的视野。而远方,变得更加诱人。随着周边细琐事项的漠视,我们会越来越向内心寻求问答,也就是寻求意义。学者们的出现正好呼应了这一需求。第二个,就是年轻人成长的社会化方式的变化。廉思教授的《思行者》就说过,年轻人的 “社会化” 有两种。一种 “生产型社会化”、另一种 “教育型社会化”。像我父母那个年代多属于 “生产型社会化”,我小时候就经常会听到父母小时候跟着劳动、生产的故事,什么偷西瓜啦、放牛啦、收麦子啦,会觉得他们怎么那么有意思。而到了我们这个年代,更多的属于 “教育型社会化”。像我从小读书长大,所有的记忆都是和上学有关,课余生活也几乎被培训班、辅导班所填充,几乎是一直处在教育系统里。这样之后很容易对现实事物缺乏真实的了解、也不知道它本身实际操作的步骤,而喜欢去追寻一些空泛的、像要填政治问答题的细节。比如 “你是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的?” 这种非常具有实操性的话题。像原本很自然的劳动变成了社会实践课上的要求,变成了给妈妈洗脚、打扫卫生这种指标性的东西,久而久之,也就在两代人之间形成了差异。这样的坏处,有两点。第一是与现实割裂,过度在意评价。这样教育型的社会化,很容易形成一种笼统空泛的印象,对于实际操作非常恐惧。同时因为在评分系统里待太久,就会非常重视他人的评价,而忘记重要的是做出成果。第二点就是 “同辈交往” 代替了 “长者相伴”。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会跟着兴趣相仿的同龄人一起交流,在网上形成兴趣部落。像最近几年都非常轰轰烈烈的粉圈和成团等现象,都是有一批有相同兴趣的年轻人,自己抱团、互相攻击、过度防御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现象。和在 “生产型社会化” 的年轻人相比,“教育型社会化” 的年轻人更加愿意和与自己同年龄段的有着相同取向的人沟通,所以 “社会化” 的进程会慢于与年长几岁的人一起长大的人,显得更加低龄、幼稚。而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针对社会出现的种种疑惑和不解,也慢慢的涌现和凸显出来。年轻人习惯性求助于网络,寻找和自己有相同问题的人,并且试图给出答案。但那答案肯定不会非常非常满意,迷茫时也无人申诉,直到学者们的出现。不管是 “读书到底有没有用?”、“我对人生的想法到底对不对?”“对未来我应该抱有怎样的期待?” 等一连串还未来得及被解决的问题,通过学者带有光环式的发言和科技的便利,最终到达还在迷茫的年轻人身边。那么,新一代新青年们能够通过学者们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救亡之路了吗?这个问题,我想还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就像不管你在网上多么的活跃,最终也只能对身边的人产生深刻的影响,对其他人无法有更多的接触。那些瑰丽的话语、感动你的真诚,隔着网线和距离到底有没有对你自己产生深远的影响,只有你自己知道。如果只是停留在大脑皮层的兴奋层面,无法真实的落实在行动,也许最后也只是一种热血沸腾的骚动而已。真诚的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区分,最终做出主动的选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验证他们所说的话。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5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5.0心就那么点大,谁在身边就对谁好点吧✨借清秋的夜,揽一池星河入梦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我点燃烛火温暖岁末的秋天🍁忽然想问你一些有关秋天的事: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冷了要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秋天喜欢我忽然想问你一些有关秋天的事: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冷了要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秋天喜欢我忽然想问你一些有关秋天的事: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冷了要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秋天喜欢我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我点燃烛火温暖岁末的秋天🍁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我点燃烛火温暖岁末的秋天🍁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我点燃烛火温暖岁末的秋天🍁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赞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4.0“现在是娱乐至死的时代。人是一种追求意义的动物,娱乐能够带来一些意义,但比较容易耗尽。在意义耗尽后,人们自然就想去找更深刻、更容易带来持久意义感的东西。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是为社会创造意义感的一群人。相比于短平快的快餐,他们能带来更有滋味的东西,人们可能会产生兴趣。但在泛娱乐化的时代,知识分子为了获得更多受众,也只能下沉、表达得更浅一点。浅化的过程也会让意义有一定耗损,但这种耗损还是可接受的,因为知识分子做的这种公共表达,首先不是为了传播特别深刻的知识,而是为了告诉社会,还有这样的知识,问题还可以这样思考,如此这般后,能够把用户吸引过来,让他们愿意主动去找专门书籍来阅读,就大致达到目的了。”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赞分享「微信」扫码分享 - 加载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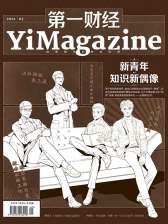 电子书
电子书第一财经(月刊 2021年05期)
关于知识分子的价值,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在著作《知识分子的背叛》中对其有3个特征总结:他们是静态的;他们是大公无私的;他们是理性的。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这三点都是稀缺之物。也因此,当它们出现,时代中最渴求答案的那个群体就会给予热切回应。这个群体,就是年轻一代。 成长于互联网的这代新青年,正以他们独特的、前所未有的方式,追随他们看到的知识偶像。而被视为“偶像”的知识分子,也需要学习全新的媒介传播和代际沟通方式,在共同文本日渐消亡的情境下重构公共议题。 某种意义上,在任何一个时代,知识阶层借助新媒介进入公众视线,扩充的都是一个“思想和知识的市场”。无论他们“卖”什么、能否让更多人受益、可否改善整个市场的水平,“进入市场”这个行为本身,就有价值,毕竟,没有人会抗拒一个开放、丰富、热闹的市场,知识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