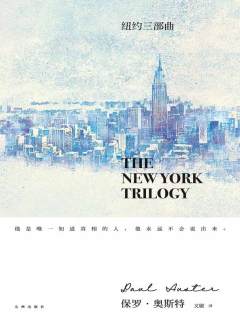《玻璃城》《幽灵》和《锁闭的屋子》这三个故事均以纽约为背景,套着侦探小说的外壳,三者均以 “失踪与寻找” 为线索,最终指向自我身份、写作本质和语言局限性。
在语言、观察与文本的迷宫中,“真实” 不过是幸存于废墟中的一场叙事,而人类注定是这场叙事的囚徒与共谋者。
《玻璃城》丨故事吞噬了讲故事的人
《玻璃城》中,丹尼尔・奎因是推理小说家,以笔名威廉・威尔逊创作侦探小说,受雇调查案件时又化名为侦探保罗・奥斯特。他在小说中扮演了三种角色,逐渐分裂成他们,最终消解于自我异化。
推理小说家:丹尼尔・奎因
一切始于一个深夜的错位电话 —— 原本要找私家侦探 “保罗・奥斯特” 的电话误打到他家中。出于作家的好奇心,他冒充侦探保罗・奥斯特接受了委托,开始跟踪刚出狱的老斯蒂尔曼。
那时的奎因已经不再写诗、剧本和评论文章了,他的一部分随着丧妻丧子已经死掉了。现在的他通过创作不费脑筋的推流小说进行自我疗愈。他认为推理小说是威廉・威尔逊的事情,所以他对那些作品也并不关心。
接收委托后,他又开始扮演侦探。最终,委托人消失,案件未破,奎因最终流落街头,成为纽约街头的无名流浪者。
侦探:保罗・奥斯特
那个错位的电话称他为保罗・奥斯特,奎因便扮演了他。
“保罗・奥斯特” 既是奎因扮演的侦探,又是故事中的一位作家,还是小说外部的真实作者,形成虚实嵌套的镜像结构。
故事中,虚构对现实进行入侵,当故事中的奎因见到故事中的奥斯特时,“他觉得奥斯特就像是在拿他失去的东西来奚落他,他对此的反应只有嫉妒和怨忿,一种撕裂般的自哀自怜。是的,他也想有这样一个妻子和这样一个孩子,整天坐拥书城高谈阔论,身边围绕着溜溜球、火腿煎蛋和笔。”
侦探奥斯特的任务就是通过监视斯蒂尔曼掌控真相。
斯蒂尔曼有一个红色笔记本,上面记录着无法被理解的 “新语言”。奥斯特也有个笔记本,前半部分记录着他观察着的斯蒂尔曼的一切。至到委托人消失,侦探仍旧不断的记录,日以继夜的记录,但是内容已经不是他的观察对象了,是奎因早已不在写的东西。是星辰、是地球、是一块石头、一片湖、一朵花,是一切。
笔名:威廉・威尔逊
奎因以威廉・威尔逊为笔名创作推理小说,每年出版一部,以此维持生计。奎因并不关心小说,因为那是威廉・威尔逊的事情。
奎因曾经遇到一个读着他第一本系列小说的姑娘,姑娘只是把读这本书当成是消磨时间,但因他仍保持着奎因,而不是威廉,这样读他的书的方式使他感到痛苦。
奎因在监视的过程中,逐渐失去对威廉・威尔逊这一身份的掌控。
身份只是自我一个空洞的符号,而语言也仅是约定俗成的游戏。
《幽灵》丨他者吞噬了主体
私家侦探布卢(
Blue)受匿名雇主委托,监视一名独居的作家布莱克(
Black),任务要求他每天记录布莱克的日常行为,但禁止与其直接接触。
布卢在长期的窥视中逐渐发现,布莱克的生活极度单调,几乎只做两件事:写作与阅读《瓦尔登湖》。
后来布卢的监视行为逐渐失控,他开始伪造报告、潜入公寓,最终布莱克消失、布卢陷入身份崩溃。
蓝与黑
蓝色(
Blue)的冷寂的布卢作为私家侦探,其名字 “蓝” 象征旁观者的疏离感。他试图通过监视保持客观,却逐渐沉溺于被观察者的世界,陷入自我怀疑的深渊。
黑色(
Black)的虚无的布莱克作为被监视的作家,其名字 “黑” 指向神秘、不可知。他的生活单调,却如同一片黑洞。
奥斯特通过颜色命名,暗示布卢与布莱克的名字不过是偶然的标签,二者被随机赋予符号,其本质都是相同的。
当布卢最终陷入身份崩溃时,蓝色与黑色的界限彻底消失。
蓝
→黑
初期,布卢的监视报告以简洁、准确的语言记录布莱克的日常。
在长期窥视中,布卢逐渐模仿布莱克的行为,购买同款打字机、阅读《瓦尔登湖》,甚至开始思考布莱克的写作内容。
布莱克单调的生活让布卢的监视报告失去意义,他伪造内容,最后又潜入布莱克公寓、偷阅其手稿。
最后,布卢杀死了布莱克,就像自己杀掉了自己。
自我通过他者建构,而他者本身是虚幻的倒影。
《锁闭的屋子》丨文本吞噬了作者
我收到童年好友范肖的遗书,得知范肖已自杀身亡,并委托我处理其未发表的遗稿、照顾其遗孀苏菲及儿子。范肖的遗稿包含小说、诗歌与日记,其作品出版后大获成功,使我名利双收。
我开始调查范肖是否真的死亡,发现他可能隐姓埋名流浪。在追寻过程中,我成为他的替身。最终,我将范肖的笔记本一张一张撕下,丢进垃圾桶。
撕毁笔记本表面上是对范肖控制的挣脱,实则揭示了更深的困境。范肖的文本早已内化为我的一部分,销毁行为更像是一种弑神仪式。
但这种救赎是徒劳的。
存在与吞噬
《玻璃城》中奎因的 “存在”:作为推理作家和侦探扮演者,奎因通过扮演侦探保罗・奥斯特赋予自己存在感,但这种存在是表演性的 —— 他依赖 “监视斯蒂尔曼” 这一行为维系自我。
《幽灵》中布卢的 “存在”:作为监视者,布卢的存在依赖于对布莱克的观察与记录。他的日记、行动甚至思考,均以布莱克为坐标轴。
《锁闭的屋子》中我的 “存在”:我通过继承范肖的遗稿和家庭,叙述者获得了名利与社会身份。此时,我的存在依附于范肖的文本遗产。
存在是他者凝视下的即兴表演,一旦凝视消失,表演者的存在即崩塌。